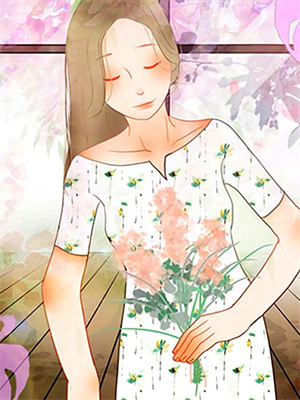简介
想要找一本好看的宫斗宅斗小说吗?那么,我捡的侍卫权倾天下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。这本小说由才华横溢的作者流光笔迹创作,以姜梨萧寒为主角,展开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。目前,小说已经连载让人期待不已。快来阅读这本小说,114537字的精彩内容在等着你!
我捡的侍卫权倾天下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天破晓,昨夜的潮气还趴在砖缝里,不肯散。城南的街沿被清晨的阳光轻轻一推,亮了一道细细的边。姜梨把门闩轻提了半寸,放下,再提,再放——那一缕极轻的金属声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圈,像把一张薄纸压稳。
阿寒已经醒了。他把昨夜叠得整齐的被翻开一点,坐在地铺边缘,神情安静。姜梨望他一眼:“起来,换身衣裳,随我去市上走一遭。”
她从箱里摸出一套洗到发白的青灰短褂,袖口与衣襟都被旧时的针脚牢牢地咬住。她又抓出一块窄头巾,颜色不显,边缘磨得有些毛。
“先把头发理一理。”她道。她没有剪,只把他鬓角过长的一缕收拢,用细线在耳后缠了一道,线很薄,颜色接近发色。然后,将头巾斜斜一压,露出额角一指宽。那露出的那一指宽,恰好让他看起来更年轻,也更像一个在外跑活路的少年。
她退后一步,打量他:“从今日起,屋里你叫‘阿寒’,屋外——”她顿了顿,像在挑一个合适的字,“叫‘凉生’。凉为凉,生为生,风凉人清,一口气活得长些。有人问你是谁,你便说是我远房的外甥,来投我学些端茶递水,替我跑腿,住几日看缘分。”
阿寒看着她,唇很轻地动了一动,发出一个几不可闻的音节:“凉……”他停,像在把这个字在口腔里放稳。随后,他挺直背,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还要记两件。”她抬手,伸出两指,“第一,你在外面少说话,别人问你,你先看我。若我点头,你再答;我不点,你就当没听见。你可以装耳背——耳边常年熏药,听不真。第二,若我不在身边,你不能答的,你就笑一笑,指指我屋门,说回头问‘姜娘子’。”
她把“姜娘子”三个字说得柔和,像铺在泥地上的一层草席,既不硬,也不滑。
阿寒凝神听,掌心轻轻在大腿上按了三下,节奏与昨夜相同。按完,他抬眼看她。
“很好。”她笑意微浅,“手势也得有,不是人人都懂我们的三下。你看。”
她把手抬到胸口高度,掌心向下,先是稳稳地压了一下:“这是‘别动’。”又将两指朝后勾:“这是‘靠后’。”拇指扣住食指第二节,捻一下:“这是‘有人盯’。”最后,她把食指在桌沿轻轻点了两下,停,再一点:“这是‘叫停’。你若心里不安,也可以这样提醒我。”
她一遍遍做,速度极慢。每一个手势落下时,指尖的力量都是均匀的,像一把细细的秤,把动作放在秤盘上称一称,轻重刚好。
阿寒看着,跟着做。他的模仿几近无误,只在“扣指”的那一下,力道大了半分。她伸手去轻轻按住他的拇指,声音压得很低:“轻些,扣得太紧像要拔刀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,那一声像风里的一根很细的草,压下去,又弹回来。
她又道:“还有你的步伐。走路不要总踩在阴影里,偶尔要走到光上,让人看见你的脚。你是‘耳背少年’,不是‘影子里的刀’。记得吗?”
他点头,眼里的黑像在灯芯上爬过一层温的黄。
说定这些,她把门开了半扇,侧身让他先走。阳光顺着门缝挤进来,落在屋内的案上,把那把小刀的刀鞘照出一道浅浅的光。
城南的早市还未完全闹起来,只有最早的一批菜贩挑着担,慢慢地在巷子里摆开。卖布的在棚下垫了一床旧被,把整卷整卷的粗布从肩上卸下,落地时发出沉闷的一声。卖鞋的把麻底布面鞋挂在横杆上,鞋尖排列得像一串串的黑豆。
姜梨带着阿寒,先绕到布摊。布摊老板见她来,笑得眼睛都眯起来:“姜娘子,昨儿晚那病患可好了?你那手,一摸一熬一按,怪是厉害。”
“好了些,得再养两日。”她淡淡应着,指了指角落里一卷旧青布,“这匹可卖整匹?不要新的,要旧色。”
老板笑:“你偏爱旧色,省得招眼。成,给你剪三尺,可够做一件外褂。”
她点头,又看了一眼阿寒,随口道:“这是我外甥,耳背,叫凉生。”
老板顺着她话头看过去:“凉生?是个清亮名。小郎儿,跟着你姨学本事就是福。”
阿寒听到“清亮”,眼睫微微动了一动。姜梨似不见,只从草篓里摸出两枚铜钱按下。拿布时,她故意把布的边在阿寒手背上擦了一下:“粗。不扎人,穿着耐。”
他们又转去卖鞋的摊。鞋摊伙计是个利索的小姑娘,叫小钗,跟姜梨熟,笑吟吟地把一双最不显眼的灰布鞋递来:“给你自己?看你外甥脚,像练过路数,鞋底要厚点才禁磨。”
姜梨看了阿寒一眼,漫不经心道:“给他。他在我这儿跑腿,脚步要稳,不许摔。”
小钗“哦”了一声,手下倒麻利,把最厚的麻底翻出来,又把鞋尖略略压扁,显得旧些。
买完这两样,她又去草药摊上抓了艾叶与臭黄叶,装在最上层。艾叶的气味热,臭黄叶的气味淡,却绕,二者混在一起,会掩掉一点血腥与金属的腥凉。
这一圈下来,日光爬上檐角,市上人声多了起来。有人挑担喊,卖糖的敲着小铜片,叮叮当当地响。邻里间打招呼,消息也就跟着走。
“姜娘子,这是谁家孩子?”一个圆脸的妇人从对面摊子探过头来,笑里带着一点打量。
“外甥。”姜梨回。
“哪门外甥?你娘家在南边,哪时冒出来个北口音的外甥?”妇人是张二嫂,嘴快,眼也快,第一眼便盯上了阿寒头巾下露出来的那一指宽额角。
姜梨不急不缓,淡淡笑了一下:“远房,过路,暂住两日,借我手边差使使。”
她说话时,手没停,从草篓里摸出一小束桂枝,递给张二嫂:“前两日你咳嗽,早晚煎这个,别总舍不得火。”
人情是一枚温暖的铜钱,递出去,话就软三分。张二嫂接过桂枝,嘴上还要再问:“这孩子怎么不说话?”
姜梨把手抬了抬,掌心向下,轻轻一压:“耳背。”她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,笑意浅,“跟我在药里熏了多年,什么都听不仔细。慢慢养。”
她把“耳背”两个字放得很平,不尖不硬。张二嫂“啧”了一声,便转了话头,去同旁边的卖布娘们儿闲话。她的眼珠还时不时往这边溜一溜。
回程的路,阳光从巷口倾下来,落在地上的水渍边缘,镶出一道亮。阿寒走在内侧,偶尔会很自然地把身子再往里一寸,给她遮去从转角撞过来的光。姜梨走着,似不觉,心里却收起了一笔——他的步伐已经在往“光里走”与“影里避”的尺度间找准那个平衡。
出巷口时,她忽然停了一瞬,食指极轻地在篓沿上点了两下,停,再一点。阿寒立刻缓缓靠后,脚步不快不慢,恰好让他们一前一后错开半步。
对面两名身着皂衣的差役从街口拐进来,手里拿着牌簿,正一家家地看门脸。那牌簿上压着红封皮,角被翻得卷起。二人目光扫过时,是一种并不特别,却很擅长挑出“不同”的眼。
姜梨像是不曾看见,抬手去捋了一下头巾,把它从额角再压下一指宽。她的步子没有停,只在经过油坊门口时,顺手将篦子般的门帘挑起一点,让两人的身形落入油坊门板投下的那道阴影里,然后,不动声色地让影子与光再度交接。
差役离他们不过两丈时,忽然被谁叫住。有人把昨夜丢失的鸡往他们手里塞了一把羽毛,嚷嚷着要给个说法。二人被拖着,暂时没工夫再看过来。
姜梨收了手,淡淡道:“回去。”
回屋后,她关上门,仍旧是那半寸的闩,提起、落下,清脆的两声,像落在心头的两个点。她把草篓放下,把买来的布摊开,又拿出针线盒,开始在旧短褂里缝一只暗袋,位置在衣襟内侧靠近肋骨处。
“你身上那半玉,不要贴心口。”她低声道,“贴心口太显,搜的人第一下就按那里。挪到这儿,走动时不会磕到,也不易被人摸到。”
她说着,眼睛不抬,针在布里进进出出,针脚看似笨拙,实则均匀。她故意让最外层的线露出两针不齐的痕,像个不太会女红的人匆忙缝的。
阿寒看她,目光里有一瞬极细的光,像一滴水落在石面,没声,却留下痕。
暗袋缝好,她把那半截玉佩从阿寒手中接过,用一小片粗布包了两层,再塞进去,按了按,平。她没有多看那玉,只看布的边缘是否贴合。
“来,”她把笔墨拿来,摊开一张废账页,“写一个字。”
她在纸上写了一个“凉”字,笔划收放之间干净利落,又写一个“生”。“外头,你叫这个名。你不写也无妨,你在心里记牢。”
阿寒用指尖在纸的空白处跟着比划。他的手指很稳,指腹在纸上滑过,像一盏灯的影掠过墙面,不留痕,却照过。
她看他比完,收起纸,叠了两叠,塞进账册的夹层里。
午时刚过,巷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声音不重,却直。紧接着,门板上被叩了两下,不轻不重,正正落在门心。
姜梨抬眼,目光与阿寒一对。她掌心向下,轻轻一压:“别动。”又两指一勾:“靠后。”随后,她放下闩,开门。
门外站着三人,两个皂衣差役,另一个是里正。里正与她有一面之识,面色尴尬:“姜娘子,抱歉,有公事。”
差役把红封皮的牌簿翻开,冷冷道:“昨夜二更北门外有打斗,有人受伤逃入城内。今早我们按各坊各巷查人。有人报说你屋里多了个少年,要问一问。”
邻里几个爱看热闹的已经远远地站在拐角。张二嫂也伸着脖子,眼睛亮得像豆子。
姜梨把身让开一寸,侧让出门口,却不让全开。她语声温温:“大人要问,问便是。只是我屋里今早熬了艾叶臭黄叶,味冲,怕污了几位衣襟。”
她话音未落,屋里已经有一股热辣辣的味道扑出来。那味不是单一的艾蒿味,是被她用一撮陈皮与几块生姜皮提过的,层次一叠一叠,像热雾里混进一条细细的辛线,直往鼻腔里钻。
两名差役微微侧头,像下意识要避。为首的那个仍撑着面子,冷声道:“我们办的是差,不择地方。”
“自然。”她笑意不深不浅,“几位若不嫌弃,进来坐。只是我这儿有个发热的,昨夜刚收,今晨还在汗里,怕冲。”
她语气里的“发热”与“汗里”,带着医者的平常。差役的目光越过她,看向屋内。屋里并不昏暗,灯芯剪短,只留一指宽的光;灶边蒸着热,桌上摆着几味药,案角压着一柄小刀——那刀鞘被布包着,只露出一截不锋利的背。
里正掩了掩鼻,冲两名差役使了个眼色:“问便问,快些。”
差役跨进门,一脚踏在门槛内侧。他的脚步惯性是城中人的,稳,直,不绕。第二名差役往左一分,目光落在屋角,像是要先把屋里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用眼扫一遍。
姜梨站在屋中,侧身,半挡住了里屋的门。她抬手,将掌心向下按了一下,指尖微不可察地带了个弧——那是只给屋里的信号。
里屋,阿寒靠后,站在光影交界。额角的一指宽被头巾遮住了大半。他的眼垂着,看似在看地,事实上余光贴着每个人的脚,数着步伐与角度。他的手没有去摸刀,指尖轻轻抵住桌沿,像抵着一条不该弹出的弦。
“说那少年是哪来的?”为首差役翻了翻牌簿,冷道。
“远房外甥,乡下过来,耳背。”姜梨如实说了她预备好的那一段,“来替我跑腿、洗药,住几天看缘分。”
差役看她一眼,又看向阿寒:“叫什么?”
“凉生。”姜梨答。
“姓呢?”
“随我姓,姓姜。”她淡淡道,“没上谱,记个名好唤。”
“昨夜在何处?”
“在我屋里。”她伸手,指了指灶边那只还未洗净的药罐,“发热。夜里出了一床汗,我把窗缝塞了两层布。邻家若不信,问问对门的王大爷,他夜里咳,半更还让我去看过两眼。”
说话间,她把那股子“热”的味道往外掀了一掀,仿佛真怕人闻不到。差役却被熏得眉心微蹙。
第二名差役斜了斜目光:“少年,把头抬起来。”
阿寒依言,慢慢抬头。那一抬,不急不缓。他的眼没有直直去撞那差役的目光,而是略略偏开,停在差役肩头的衣缝处,像一个耳背的人习惯性地去看人说话的口形与肩膀起伏。他的唇动了一下,却没有出声。
“会说话吗?”
姜梨抢在前头:“能说两句,耳背,反应慢。你若用力喊,他会缩。”
她把“缩”字说得极轻。恰在此时,里屋一个小炭盆里“啪”的一声,爆出一点星。阿寒的肩很轻地动了一动,又稳住。
为首的差役冷冷盯着他手:“做什么活?你手上的茧,不像挑水,是把刀。”
姜梨笑了笑,走过去,拿起桌上的那把小刀:“大人眼睛尖。是刀,不过是割药草用的小刀,柄细,时用时搁。他跟我学,拿刀割草割得多,手上自然起茧。您看。”
她把刀递过去,手指把刀鞘往上推了一分,只露出钝钝的背,又立刻推回去。那动作中规中矩,毫无“兵气”。
差役接也不是,不接也不是,最后还是没接,冷哼一声:“伸手过来。”
阿寒把手伸出,掌心向上。掌纹细密,中央一处浅浅的蹭伤已被药粉糊平。差役用指背撞了撞他的掌心,想看他有什么躲避的本能。阿寒不动,只是掌心很自然地随着那一下轻轻弯了弯,像是被热气一拂。
“昨夜,二更,北门外,打斗。”差役像是念帖,“城里有人看见一少年从北门影里奔进来,衣裳湿,肩上染血。你身上有伤没有?”
“有。”姜梨应得快,“烫伤,昨夜换药,今晨刚结焦。何处,我可不便当街示人。若诸位非要看,不如明日再来。伤在臂弯,我解开你们也嫌麻烦。”
她把“麻烦”两个字说得轻,像替对方省事。为首的差役鼻翼动了一动,似要压下被艾叶与姜皮勾起的生理厌。里正在旁轻咳了一声:“姜娘子的手艺是左近出了名的,昨夜王大爷老婆的咳就是她压下去的。她在屋里忙了一夜,若说少年在,她说在,八成就在。”
为首的差役目光一沉,还想再细查。一转头,看见门边架子上晒着的几绺草药,颜色发灰,不好看,味却冲。再看灶边那口半掀着盖的药罐,热气腾着,像一锅苦的雾。他下意识后退了半步。
“时下有小疹子在南边起头。”姜梨不紧不慢补了一句,“虽不必惊,但也忌与发汗者靠太近。几位若无须细看,便只问个名录,放我与他清静一会。再者,若真要查,他耳背问不出什么,耽误你们工夫。”
她把“耽误工夫”四字往前推了一推。差役互相看了一眼,为首的把牌簿往里一按:“名录上写‘凉生’,暂住。若有人问起,里正你做个签。”
里正忙不迭点头:“成成。”他抽出纸笔,手略抖,却还是写下了“凉生暂住姜家巷三号,耳背,帮工。”
这一场似乎就要过去。谁知第二名差役忽然像想起了什么,目光一收,落在阿寒的侧脸上。他一步向前,手里那根细竹尺举起,像要挑起头巾的一角:“把这头巾——”
竹尺还未碰到,姜梨已笑,往前一步,把他手轻轻挡了一下,挡得恰到好处,不硬:“大人,头巾下是烫伤未好,揭了容易沾。若您要看,我明日给您送去衙门,看个明白。今日揭了,粘上去,可真叫麻烦。”
她说着,手指捻起灶边的一撮艾叶,轻轻在袖口一揉。味更重了。差役鼻子一酸,眼睛不由自主眯了一瞬。这一点不受控的生理反应,叫他的气势轻了半分。
他哼了一声,收回竹尺:“谨慎些。”
“多谢几位体谅。”姜梨退半步,侧身请,“慢走。”
几人出门时,张二嫂“刷”地把脖子缩回去,又装作在看隔壁的蔬菜。差役走了两步,为首的忽然回头:“昨夜北门外丢了样东西。半块玉。若谁见着,莫要藏,藏了的,犯官条。”
“半块玉”三字在屋里轻轻跌了一下,像落在水面的一片薄叶,旋即被热气吞没。姜梨神色不变,行礼:“记着了。”
门合上。她提起门闩,落下,静静地站了会儿。屋里的热气仍缠,艾叶的味压着人。她回身,望向里屋。
阿寒从影里走出来。他的肩膀从紧到松,又在靠近她时别过脸,极轻地咳了一声。那声咳不是为气味,是为压着的气被放开时,心口里不知该放在何处的一口气。
姜梨看着他,抬起的手缓缓落下,掌心在空气里拍了拍,像拍火背:“好。你刚才做得很好。”
他眼里的黑还在收,像潮水退到岸边,露出被水打磨过的小石。过了一息,他伸出手,指尖在桌沿上叩了三下:短、短、长。
她回了三下。
她走到窗边,把塞在窗缝里的布抽了一层,让风进来,风把味吹淡。她把灶边的药罐揭盖,锅里的水“呼”的一下吐了口气,屋里像有人终于说了声“累”。
“来,”她招手,“我们把外头用的‘问与答’再过一遍。你站这。”
她在屋里拣了四个位置:门口、案前、灶边、里屋门。她站在门口,扮作差役,声音冷:“你是谁?”
阿寒站在案前,目光略偏,唇动:“凉生。”
“从哪来?”
“北边。”
“北边哪?”
他稍稍停了一息,目光看向她。
她点头,他才慢慢道:“北郊,河沿村。”
“来做什么?”
“帮工。”
“会做什么?”
他伸手,指了指灶边:“挑水、烧火、晒药。”
“昨夜在何处?”
“屋里。”
她换到案前,扮邻里:“你是她什么人?”
“外甥。”
“耳背?”
他点头,不说话。
她又换到灶边,扮卖布娘们:“几岁?”
他停,眼睛抬起又落下,像在数:“十七。”
“姓什么?”
他抿唇,极轻:“姜。”
她在里屋门前停下,收了戏。她把手掌心向下,压了一下:“好。你记得有一处最要紧。外头所有问,你都可以慢一呼吸,再答。慢半拍,不是弱,是稳。”
她顿了顿,又道:“我们还要再加两样。第一,你的步伐,要在‘不惹眼’与‘不怯’之间。你走得太轻,人疑你;你走得太响,人也看你。第二,你遇见小孩子,微笑一下;遇见喝醉的,绕开一寸;遇见狗,停半步等它先看你。记住?”
他一条条在心里过,指尖又在案上叩了三下。她知道他是在告诉她:记住。
午后偏西,阳光在窗纸上推移。巷子里有人撑起竹帘,把一笼笼馒头端出来晾。卖饼的吆喝声远远地飘过来,又被某个拐角接住,切了一半,回声短。
姜梨把买来的布按样子裁开,给阿寒做了一件外褂。她做得慢,针脚故意大,像心急的人糊出来的活儿。阿寒坐在旁边,看她,偶尔伸手把线头递过去。他递线时,指尖很稳,动作极轻,像怕掀起什么。
“你若在外头被人拦住,要逃,不必朝正街跑。你走鱼行后巷,那里地滑,追的人脚下会打滑。”她随口说,像在聊天气,“你若要藏,先看门牌,奇数的后墙多有猫洞,偶数家的后墙多是砖整墙。”
她说的都是这片坊间的“寻常”。这些寻常,是她在这屋住了几年,日日走,年年看,自己踩出来的地图。
阿寒听着,眼里那一点亮像一粒不滚的砂,静静地在心底一处。他把这片地的“寻常”一条条在心里刻起来。
暮色将近时,门外又有影掠过。不是差役,是邻里。一阵窸窣,像有人在墙根说话。
姜梨没有去看,仍旧把线头抽过,打了个结。她只轻轻点了桌面三下:短、短、长。她没有看阿寒,但她知道他听见了。
夜色落得快,屋里点灯。她把灯芯掐短,仍旧只留一指宽。她把饭煮了,仍是粥与一碟青菜。二人一人一碗,吃得不快。吃到半碗时,门外忽然“笃笃笃”三声急促的叩门,迅疾,短,不同于方才差役的平稳。
她与阿寒对视一眼。她起身,未开门,先在门板内侧问:“谁?”
外头一个细尖的声音:“我、我家鸡又不见了,我来问问邻里有没瞧见,顺道……”话头拖得很长。
是张二嫂。她顺道的,当然不是鸡。
姜梨把门开了一指宽,站在门后:“我今儿忙,没见鸡。你若真要找,去油坊问,油坊门口猫多。”
她不给开门的由头,也给了人台阶。张二嫂“哦”了一声,眼睛还往屋里探。她嗅了嗅:“你屋里今儿味真重。”
“熬药。”姜梨笑,“二嫂若不怕苦进来坐,我给你熬点止咳糖。”
“不用不用。”张二嫂连忙摆手,脚步往后挪了一寸,“我回头再来。”
门又合上。屋里恢复静。
这一日的绷,到此才稍稍松下去。姜梨把碗搁下,捏了捏眉心,忽然笑了一下:“第一次,算是过了。”
她看向阿寒:“你方才的‘看肩,不看眼’做得好。记着,眼里多火的人,肩膀不动;肩膀动得多的人,眼里火少。前者你要慢,后者你要稳。”
她说着,想起差役临走前那句“半块玉”,心里有一瞬极轻的紧。她不看阿寒,只把灯芯又掐短了些,让光再弱一点。
“我再说一次。”她声音很轻,却一字一字落稳,“身份这个东西,不是为了欺人,而是为了先护住我们。护住了命,才谈其他。你在屋里是‘阿寒’,在外是‘凉生’。你记得。”
阿寒看着她,极慢极稳地点头。他把手伸向胸口,按了三下,又伸向案面,按了三下。然后,他把手摊开,掌心向上,停在半空中一瞬,又收回。
“睡前,”她忽然道,“我们把手势再走一遍。关灯之后也要会。”
灯灭。屋里暗成一片安静的墨。她站在案前,手指在空气中轻轻划过——掌心向下,压;两指勾,靠后;拇指扣食指,捻;两点一停再一点,叫停。每一个动作都缩小到只剩下肌肉的微微收缩,像心在窗纸后面跳。
黑暗里,另一双手在与她的动作对齐。没有光,只有空气的微凉与两个人之间那点细细的默契。到最后一式,短、短、长,两人的指尖在空气中几乎相触,那一瞬,像有一粒不热的火落下,稳稳地停在两人之间。
夜半,风过巷口,吹过门缝,像有人把一把旧扇子打开,又合上。她躺下,听见里屋的地铺上那一口气一层层平下去。她闭眼前,心里把今日的每一步再走了一遍,像走在一张画好的图上。每一个拐角,他们都没有撞上。
次日天光微白,她先起,灶里火一挑,水便热。她把昨日缝的暗袋再摸一遍,线平,边稳。阿寒也起来,头巾系得比昨日更稳。她把外褂递给他,指了指衣襟:“记得,从今天起,玉不在心口。”
他点头。她又把一只最常见的布荷包塞进他袖口里,里面放了三文钱与一小包盐。“路上要是有人追问你要买什么,你就摸这个荷包,装出要去买盐的样子。盐是每家都要买的,没人多想。”
她抬眼:“再者,今日你一个人去后巷挑一担水回来,我在门口晒药。我们在光里动一动,给人看见。人看见多了,便不看了。”
她把晒药的竹匾端到门外,把草药摊成薄薄的一层,让阳光像筛粉一样筛过它们。她在门边坐着,手里拿着绳子,把草药一把把捆成小把,摆在竹匾一角。她不看远处,只看手边,偶尔抬眼望一眼后巷口。
不多时,阿寒挑着水从后巷走出来。他挑担的姿势不急不慢,肩背平,脚步稳。经过门口时,他目光不看她,只是把担子略略往外一分,给她的竹匾留出一条风。那样的一个小小动作,仿佛一条看不见的线从他经过的那一瞬拉到她的手上,轻轻一拽,叫人心口稳。
邻里看见了,也就看过去了。有人喊:“凉生,挑慢点,别撒了。”他回头,笑了一下,笑意不多,却正好。
这“一看再看”的两三日,差役又在巷口晃了两次,没有再入门。有人说北门外的案子往西坊去了,有人说其实是外地的流匪闹的。坊间的声音像风,来一阵,走一阵。她照旧熬药,照旧晒药,照旧在门口与人道早安、道晌午、道黄昏。
第三日午后,里正来门口,递了一张小小的签条:“衙门里还是要存个底。你别嫌麻烦,我给你写了他的名。你收着。”
姜梨接过,签条上写着“凉生,暂住,耳背,帮工”。字歪,心意诚。她道谢,收进账册夹层。里正欲言又止:“那差上嘴紧,临走说了‘半块玉’。你还是小心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她笑一下,把人送走。
门合上,她站在门后,背靠门,手掌在身侧轻轻拍了拍空气,像拍定一张纸。阿寒从里屋出来,在她面前停一停。
“凉生,”她刻意在屋里唤了这名字一声,“外头叫你这个,屋里——”
“阿寒。”他接。
“对。”她点头,“这两个字像两扇门。哪一扇开,哪一扇关,你自己要知道。”
她把手伸过去,掌心向下,轻轻一压。阿寒学她,压。两人的手在半空停了一息,像在一处看不见的门闩上扣了一扣。
天色渐暗,城南的风把远处的喧哗吹薄。她把灯点了,灯芯仍旧一指宽。灶里的火跳,发出极小的声音。她把药罐端下来,换上了汤锅。锅里水滚,翻出一层层的小泡。
她侧过身,看着火,轻声道:“往后还会有人来问。你记得今日的每一步。你若慌,先叩三下。你若不肯,我便替你肯。你若要走,我说‘走’时再走。不说时,守住。”
她的话不多,却像一根根细线,把屋里屋外、白日黑夜、光与影,一根根缝在了一处。缝得不紧,却不松。
阿寒站在她侧后,目光落在她的手上,落在火上,又落在门上。最后,落回到她脸上。那目光里,锋已收,影仍在,却安静。
“行则留。”她又轻轻说了一遍。
“留。”他应,极低,极稳。
灶里的火像听懂了什么,轻轻“噗”了一声。